夕阳西下,阿牛牵着老黄牛走在山间小路上。牛背上驮着一捆青草,是他刚从山坳里割来的。老牛走得很慢,时不时回头看看他,浑浊的眼睛里透着慈爱。
“老伙计,今天辛苦你了。”阿牛拍拍牛背,声音有些沙哑。他今年才十二岁,却已经独自撑起这个家。父亲早逝,母亲久病卧床,家里唯一的生计就是给地主放牛。

牛棚漏雨,阿牛用茅草补了又补,可每到雨天还是滴滴答答。母亲咳血的声音从屋里传来,他赶紧放下草料,跑进去扶她坐起来。
“娘,喝点水。”阿牛端来一碗温水,小心翼翼地喂母亲喝下。
母亲摸了摸他的头,声音虚弱:“阿牛,娘拖累你了……”
阿牛摇摇头,强笑道:“娘别这么说,等我再攒些钱,就给您请大夫。”
夜深了,阿牛还在牛棚里忙活。老牛卧在草堆上,慢悠悠地嚼着青草。突然,天空响起一声炸雷,暴雨倾盆而下。
“糟了,草料还没收!”阿牛冲进雨里,手忙脚乱地收拾草料。老牛突然站起来,用头拱了拱他的背,示意他快走。
“老伙计,你怎么了?”阿牛疑惑地看着老牛。老牛的眼睛在黑暗中泛着青光,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。
“子时山崩,速带乡亲逃命!”老牛突然开口说话,声音沙哑却清晰。
阿牛吓得倒退两步,一屁股坐在地上:“你……你会说话?”
老牛喘着粗气,牛角裂开渗出血来:“山腹早被贪官挖空,明日午时必塌!”
阿牛回过神来,发现老牛的蹄子上沾满了黑泥。他凑近一看,竟是铁矿渣。
“这是……矿渣?”阿牛心头一震,“难道有人在挖山?”
老牛点点头,声音越来越微弱:“贪官为私利,不顾百姓死活……快逃……”
话未说完,老牛突然昏厥过去,牛尾断了一截,鲜血染红了地面。

阿牛背起母亲,冒着大雨往村外跑。母亲在他背上咳嗽不止,声音虚弱:“阿牛,放我下来……娘不能拖累你……”
“娘,别说话,咱们得赶紧逃!”阿牛咬着牙,脚步踉跄。
屋外传来地底闷响,梁上落灰如雨。母亲突然推开他,跌坐在地上:“阿牛,带乡亲走!娘……娘走不动了……”
阿牛泪如雨下,跪在母亲面前:“娘,我不能丢下您!”
母亲摸了摸他的脸,声音微弱却坚定:“阿牛,你是娘的好孩子……快去救乡亲……”
暴雨如注,阿牛背着母亲踉跄跑到祠堂,抓起铜锣拼命敲打:“山要塌了!大家快逃!”
村民们从睡梦中惊醒,披着衣服跑出来,满脸疑惑。
“阿牛,你发什么疯?”地主赵富贵带着家丁赶来,满脸怒容。
“赵老爷,山要塌了!老牛开口说话了,让我们快逃!”阿牛急得声音发抖。
村民们哄笑起来:“放牛娃疯了!牛怎会说话?”
赵富贵冷笑一声:“妖言惑众!来人,把他绑起来!”
家丁一拥而上,将阿牛绑在祠堂前的槐树上。赵富贵抓起一把牛粪,塞进阿牛嘴里:“再胡说八道,喂你吃个够!”
天刚亮,一队官差骑马进村,为首的师爷李计高声道:“奉旨采矿,闲杂人等速速退避!”
阿牛被绑在树上,嘴里塞着布条,拼命挣扎。他看见官差的靴底沾着同样的铁矿渣,心头一震:“原来贪官早知险情,却为私利隐瞒灾祸!”
李计瞥见阿牛,皱眉问:“这孩子怎么回事?”
赵富贵谄笑道:“回大人,这放牛娃妖言惑众,说什么山要塌了,小的正教训他。”
李计冷笑:“山崩?笑话!本官奉旨办事,岂容刁民造谣?”他挥挥手,“继续封山,谁敢阻拦,格杀勿论!”
夜深人静,阿牛被绑在树上,浑身湿透。突然,老牛从黑暗中走来,咬断绳索。
“老伙计!”阿牛抱住牛脖子,眼泪夺眶而出。
老牛喘着粗气,伤口渗出的血在地上汇成字迹:“山神怒,需祭童男童女。”
阿牛心头一紧:“祭童男童女?难道……”
远处传来孩童的哭喊声,阿牛循声望去,见赵富贵带着家丁,正将一对童男女绑上山神庙。
阿牛背起母亲,悄悄跟上。山神庙内,赵富贵点燃香烛,高声道:“山神息怒,童男女献上,保我赵家富贵!”
母亲在阿牛背上低声道:“阿牛,放我下来……娘去引开他们,你救孩子……”
阿牛摇头:“娘,我不能让您冒险!”
母亲摸了摸他的脸,声音虚弱却坚定:“阿牛,你是娘的好孩子……快去……”
阿牛含泪放下母亲,悄悄绕到庙后。他发现庙下竟有密道,洞内堆满金砖。母亲摸到碑文,低声念道:“开山者断子绝孙!”字迹渗血如新。
山神庙内烛火摇曳,赵富贵手持青铜匕首逼近哭喊的童男女。阿牛躲在神像后,掌心全是冷汗。突然,庙外传来一声震天牛哞,老牛撞破木门冲入祭坛,断角上鲜血淋漓。

“拦住这畜生!”赵富贵厉喝。家丁们挥舞棍棒扑向老牛,却被它一蹄子踹飞。老牛挡在童男女身前,双目赤红如血:“贪官挖断龙脉,今日血债血偿!”
地面突然剧烈震颤,香炉翻倒,烛火点燃帷幔。阿牛趁机解开童男女的绳索:“快跑!往山下白柳树跑!”
“拦住他们!”赵富贵面目狰狞,却被老牛一头顶翻在地。牛角刺入他大腿,鲜血喷溅在“山神”牌位上,那金漆神像竟露出森森白骨。
山体裂缝如巨兽张开的嘴,喷出腥臭黑水。阿牛背起母亲,拉着童男女往山下狂奔。身后传来地裂声,整座山神庙轰然坍塌,赵富贵被埋在瓦砾中,只剩一只手露在外面,指间还攥着带血的金锭。
“阿牛哥,桥断了!”童女小莲指着前方哭喊。山洪冲垮了木桥,湍急的水流裹挟着碎石奔涌而下。
老牛突然冲上前,将四人甩上牛背。它浑身伤口崩裂,鲜血染红皮毛,却仍奋力跃过断桥。阿牛死死搂住牛脖子,泪水混着雨水流进嘴里:“老伙计,撑住啊!”
“去白柳树……”老牛声音嘶哑,牛尾已被乱石砸断,“树根下有生路……”
山崩地裂,泥石流如恶龙般扑向村落。老牛将四人甩到高坡,转身冲向裂缝。牛角深深插入山体,竟硬生生扛住塌方的巨石。
“老伙计!”阿牛嘶吼着要冲过去,却被母亲死死拉住。
老牛浑身骨骼咯咯作响,鲜血从每一处伤口喷涌:“吾本是守山灵兽……贪欲破封,合该此劫……”它仰头长哞,声震山谷,“阿牛,替我看好这片山!”
巨石轰然砸落,老牛化作青石雕像堵住裂缝。鲜血顺着石纹流淌,在暴雨中凝成四个血字:镇山永固。
三日三夜后,洪水退去。阿牛背着母亲来到老牛所说的白柳树下。树根处露出半截木箱,掀开竟是满满官银!箱底压着泛黄血书:
“知府李昌贪矿害民,吾以命封山,留银赎罪。见银者速告钦差,开箱之时,即李昌伏诛之日。”
血书落款处画着牛头印记,与老牛额间花纹一模一样。母亲抚摸着血书,突然剧烈咳嗽,帕子上染着黑血——是那夜吸入的毒烟发作了。
“娘,我背您去县城告状!”阿牛将官银裹进破棉袄。
母亲却摇摇头,从怀中摸出个油纸包:“这是你爹留下的《山河志》,记着龙脉走向……阿牛,娘走不动了,你要带着银子……咳咳……带着真相……”
话音未落,母亲的手倏然垂下。油纸包跌落在地,露出一角泛黄图纸,上面朱笔勾画的山形,正与塌陷处完全吻合。
阿牛在母亲坟前磕了三个响头,背上官银和血书往县城赶。途经老牛石像时,忽见石像双眼渗出血泪,在阳光下凝成血珠落入他掌心。
血珠中浮现幻象:知府李昌正与师爷分赃,密室里堆满刻着“赈灾”字样的金砖。老牛的声音在耳畔回荡:“血珠为证,贪官必诛!”
阿牛握紧血珠,对着石像重重叩首:“老伙计,等我回来给你修庙!”
阿牛赤脚奔至县衙,登闻鼓槌砸得震天响。鼓面浸着他掌心的血,每一声都像在叩问天地。衙役拎着水火棍出来,见是个衣衫褴褛的少年,抬脚就踹:“哪来的乞丐,惊扰公堂!”
“我有血证!”阿牛高举血珠,石像幻象凌空浮现——知府李昌正将赈灾官银熔成金锭,烙上自家徽记。围观的百姓哗然,衙役吓得跌坐在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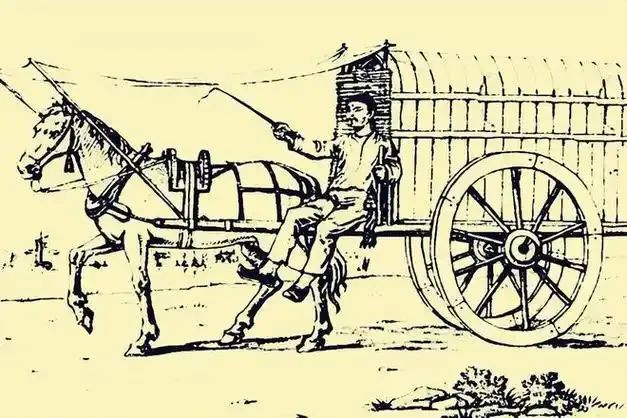
钦差周正卿的车驾恰巧路过,掀帘喝道:“石牛泣血,千古奇冤!升堂!”
公堂上,李昌面如死灰,仍强辩:“这是妖术!本官两袖清风……”
“清风?”周正卿冷笑,挥手命人抬上密道中的金砖。工匠当堂熔开金锭,内里赫然露出“赈灾专用”的铸印。
阿牛呈上母亲遗留的《山河志》,泛黄的图纸上,朱砂勾画的龙脉走向与塌山处完全吻合。周正卿抚须长叹:“《山河志》乃先帝御赐治河宝典,想不到竟成罪证!”
李昌突然暴起,拔出衙役佩刀刺向阿牛:“小畜生,去死吧!”
“哞——”堂外传来震天牛哞,一道青光撞破门扉。断角小牛犊冲入公堂,将李昌顶翻在地,牛角正中心窝。
三日后,白柳树下。钦差亲手将贪官头颅悬挂树梢,枯柳忽生新芽。阿牛将官银分给灾民,捧着母亲的骨灰跪在柳树下。
“娘,咱家的牛棚修好了。”他抓了把柳叶撒向空中,“老伙计也有新庙了。”
远处山腰,村民正在老牛石像旁建庙。石像双眼不知何时被镶嵌上翡翠,在阳光下泛着青光,仿佛灵牛复生。
十年后的清明,已成为护山郎的阿牛巡至山顶。春雨淅沥中,一头断角黄牛从薄雾中走来,轻轻蹭他掌心。
“老伙计?”阿牛颤抖着抚摸牛角,那里有道陈年旧疤,“是你吗?”
黄牛仰头长哞,山间忽起清风,吹散雾霭。漫山白柳如雪,树根处新立的石碑上刻着:
“山灵永驻,牛魂长存。”
